 打印本文
打印本文  关闭窗口
关闭窗口 专访四方田犬彦:日本电影史背后,是一部微缩的日本近现代史

日本文化研究学者四方田犬彦。采访一开始,四方田犬彦先生向我出示了一张地图。
那是一张反映东京新宿1960年代文化坐标的地图,其中最醒目的是ATG(日本艺术影院行会)的据点新宿文化会馆和近旁的小剧场“蝎座”,十几岁的四方田犬彦在这里邂逅了戈达尔、爱森斯坦、奥逊·威尔斯等影史上的杰出导演,与电影结下缘分。
从这里出发,四方田犬彦的眼界遍布众多领域,又都再度和电影产生关联。例如,他喜欢漫画家白土三平的《忍者武艺帐》,自然也没有错过大岛渚根据《忍者武艺帐》改编的电影,这让四方田犬彦和大岛渚的电影结下缘分,后来写出了《大岛渚与日本》这部优秀的人物专论。大岛渚电影中的一大主题是对在日朝鲜人群体的关注,这成了四方田犬彦一生研究的课题。1991年,他在《週刊SPA!》上刊载了“了不起的在日韩国人”特辑,其后的著作《亚洲背景下的日本电影》里甚至有专门的章节讨论在日朝鲜人问题。1994年,他还差点在韩裔导演、大岛渚的学生崔洋一的《月出何方》里出演一个嘴上对在日朝鲜人恭维不已,内心却十分鄙夷的上班族。如果出演,将是一个奇妙的双关,可惜四方田其时赴博洛尼亚大学访学而未能实现。像这样纵横交错如蛛网缠绕的文化脉络,贯穿了四方田犬彦的大半个人生。
他在朴正熙独裁政权下的韩国看过电影,也在塞尔维亚的难民营教授过日本文化。在阴冷的曼哈顿当过教员,也在酷热的东南亚做过研究。如他的名字一样,四方田犬彦是亲力亲为,走遍“四方”,看遍“四方”的学者,而后,他又选用书和电影这两种最为平等的媒介,述说他的所思所想。
刚刚推出简体中文版的《日本电影110年》便是四方田犬彦以电影为镜观照历史和社会的一个实例,在以十年为单位详实梳理日本电影历史的同时,四方田犬彦把电影放进更大的历史背景当中,开辟出许多支流,使读者通过电影感受日本社会的变化。这部关于日本电影史的小书,背后也藏着一部微缩的日本近现代史。
此次四方田犬彦先生到访中国,我们对他进行了一次专访。谈到了他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电影记忆、新世纪以来日本电影的倾向、漫改电影、大众通俗剧和互联网环境下的电影评论等话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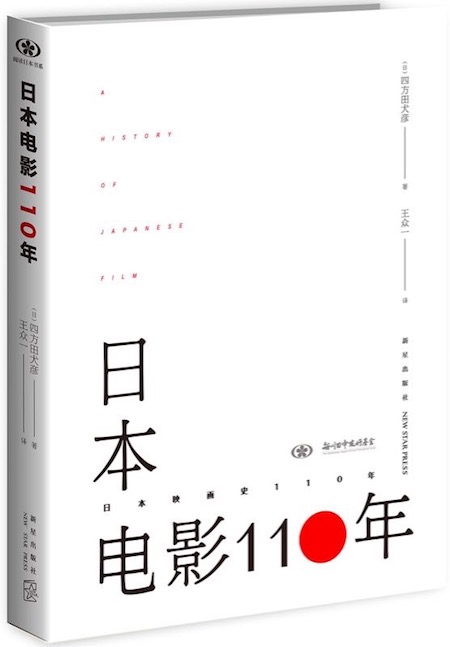
《日本电影110年》书封。[日] 四方田犬彦 著,王众一 译,新星出版社,2018年1月。
您在《日本电影110年》扉页的题词里表达了对葛井欣士郎先生的怀念。葛井欣士郎先生是新宿文化会馆的总经营者,ATG电影的重要人物。您觉得葛井先生为现在的日本电影界留下了哪些重要财产?
四方田犬彦: 葛井欣士郎是新宿文化会馆的经营者,当时的许多电影事件都和他有关。首先,他在六十年代引进了许多欧洲的艺术电影,费里尼、戈达尔、爱森斯坦等导演的作品首度在日本公开放映都离不开葛井先生的努力。
我是在1966年,13岁的时候成为ATG的会员的。我大概是会员里年纪最小的一个。为什么要成为会员呢?那是因为ATG播放的电影里经常有裸女出现,也就是说有很多18岁以下不宜观看的镜头,但如果成为会员,即使只有13岁也可以堂堂正正地走进去。我经常是逃课去的,中学的上课铃声和新宿文化会馆的广播提示音一样,所以我内心常有罪恶感。
那时,电影散场之后,大堂总有一位穿着燕尾服,戴着蝴蝶结的大叔和来往的观众聊天。我那时还是一个穿着中学校服的小孩子,总是害怕他会过来教训我,质问我为什么不好好上课。其实那位大叔是想和我搭话,问我对这些艺术电影的看法。有一次ATG的电影到维也纳电影节展映,我也去了,那位大叔——这时已经是大爷了——也出现了,自我介绍道:“我是葛井。”我这才知道当时那位让人敬畏的大叔是葛井欣士郎先生。
葛井先生的另一大功绩是大力支持了当时五大主流制片厂以外的日本独立电影和前卫电影,在1960年代中后期掀起了一股全新的浪潮。此外,他还开设了小剧场“蝎座”,那里上演的是比新宿文化会馆更加实验、更加无名的作品。我非常尊敬他,所以把这本书题献给他。
您在《日本电影110年》中提到,在21世纪的前十年,地方合作拍片的电影中介机构日渐普及,一批地方题材电影精彩纷呈。地方题材的丰富对于当今日本仍旧东京本位的现实有什么特殊意义么?
四方田犬彦: 首先,中国语境下的“地方”一词和日本区别是很大的。中国幅员辽阔,各地文化截然不同,日本的国土面积大概只相当于中国的两个省份,文化上的差距也没有那么大。但是对于日本地方的文化来说,重要的是拥有违抗“东京中心主义”的意识。
举福冈为例,福冈在地理上距离上海比距离东京还要近。上千年来,福冈接纳了许多来自中国和朝鲜半岛的知识分子、官员、贵族和逃亡者。这样的背景让福冈具备了“反东京”的属性,在福冈的视角里,东京只是一个由军事政权培植的、历史不过150年左右的城市。福冈不只把自己看作日本的城市,更视自己为亚洲的一部分,所以福冈的电影节只上映亚洲电影,美术馆主要展出亚洲的艺术品,福冈还有亚洲文化奖这样的奖项。东京在许多方面都追随美国,福冈在这半个世纪里却贯彻着截然不同的价值观。此外,冲绳也因为历史的原因而具有浓厚的“反东京”属性。
而且,这种“反叛”不只发生在地方,主张整个日本社会并不是“单一社会”的电影,比如说反映在日朝鲜人群体的电影,也在不断地被制作出来。
您在广岛现代美术馆的策展人神谷幸江女士策划的一次访谈里提到过,战后东亚各国的文化各自分离并都向美国眺望。这种情况是否随着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的东亚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发生了某些变化?
四方田犬彦: 八十年代中后期,中国的第五代导演开始在国际上崭露头角,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也掀起了艺术电影的浪潮。这些电影的广为传播,离不开它们集体走出国门,在世界范围内的电影节上亮相这样一个契机。亚洲各国接触并理解彼此之间的电影,也是借由国际电影节这个舞台完成的。当然,国家之间外交关系的改善对此也有推动作用。
稍举一例,在韩国即将对日本的影视作品解禁的前夕,遭遇到了国内一些反对的声音。这些声音认为日本电影制作精良、实力强劲,会冲击本国的电影市场。可韩国电影集体走向国际舞台也正是在对日本电影解禁之后的事。
随之而来的九十年代也是日本战后再次与亚洲以至世界各国发生正面接触的时期,您在《日本电影110年》中以“与民族性他者遭遇”来论述这一时期的一些日本电影。但是进入本世纪前十年,这种情况却改变了(“不再在电影中探索日本人身份”“只拍摄说日语的电影”),这是为什么?
四方田犬彦: 不能说是改变,应该说是这种倾向变强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了大岛渚、小川绅介、土本典昭等一批非常具有反叛精神的导演,他们始终拍摄着挑战权力的影像。新千年以后虽然也有若松孝二、原一男这样依然具有反叛精神的导演,但大型影视制作公司的电影都很保守,而且没有考虑到外国观众,所以给人以十分闭锁的印象。不只是电影,文学、流行音乐方面都有这样的倾向,用日语制作给日本人看的作品,这样便能赚钱。
我从中感受到的是现在日本的年轻世代对他者、历史、政治的不关心。我做了三十年的大学教授,这三十年感受到的学生的变化,最明显的一点是外语能力的下降,然后是对出国旅行、留学所表现出的热情的减退。甚至,有海外生活经验的人会被其他人排挤,日本现时的社会认知里排斥这种对其他族群的文化和价值观产生共鸣的人。
日本的漫改电影拥有相当长的历史。进入新千年,漫改电影每年的制作数量不断增加,现在可以说是“漫改电影热”的时期。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您认为真人化了的漫画作品会对电影这种媒介产生何种影响?
四方田犬彦: 漫改电影热并不是一种新的现象。日本的电影有不少改编自其他的艺术形式,一开始是歌舞伎,然后是新派剧、通俗剧,再然后是大众小说、落语,漫画也在此列,并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成为改编的主流,算下来,漫改电影的广泛流行已经持续了半个世纪。
不过,漫画自身的形态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变化。直到六十年代,都是由漫画家自己构思故事、设定场景并作画。到了七十年代,大型的出版社自己培养独立脚本作者(漫画原作者)为漫画构思故事、设定场景。漫画家只负责作画,不再是独立作者。所以,电影用于改编的故事其实来自于这些独立脚本的作者,“漫改电影”的定义发生了变化。
重点在于,只要是有趣的,能吸引观众的故事,电影就会拿来为我所用。川端康成的文艺小说也好,松本清张的推理小说也好,哆啦A梦的漫画也好,只要有票房保证,能受欢迎,就可以拿来用。在这个意义上,漫画并没有改变电影的状态,电影本身就是这种带着趋利性质的媒介。
漫改电影和通俗剧之间有什么可以相提并论的地方么?它们似乎都拥有一个广泛的受众群体,但高眉的电影观众对此似乎又评价不高,也无法进入主流评论的世界。
四方田犬彦: 首先必须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何为通俗剧。与通俗剧对立的是悲剧,所谓悲剧,是指主人公在超越性的力量之前败北的故事。通俗剧是法国革命时期诞生的剧种,其间没有超越性的力量,它讲述的是发生在一般人之间的以爱情、仇恨、争夺等为主题的故事。
“悲剧”这个词虽然带着一个“悲”字,却没有“悲伤”的意思。观众看完《哈姆雷特》《俄狄浦斯王》这样的悲剧之后并不会掉眼泪,通俗剧最重要的特点则是让人流泪,普通人也好知识阶层也好,看了通俗剧一定会哭。
截至目前,通俗剧的研究比起喜剧、悲剧等其他戏剧类别却落后许多。通俗剧明明让许多知识阶层感动落泪,他们却选择性地遗忘了这些体验,纷纷看不起通俗剧,以彰显自己知识分子的身份。实际上,能唤起人类内心情感的许多文本都可以视作通俗剧,这并不仅限于演剧范畴,小说里也有不少的例子,中国的《红楼梦》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型的一齣通俗剧。
漫改电影和通俗剧的级别不同,通俗剧是讲述故事时的一种讲述方法,漫改电影则是一种影像类别。通俗剧的表现可以是动画、漫画,当然也可以是漫改电影。所以我觉得你的问题本身提得不对。
您所著的《亚洲背景下的日本电影》一书中有一篇《从电影史的记忆中解放出来》,文中提到,“随着录像带的普及,某时某地看电影的记忆和体验的固有性全部消失,变得随手可得且具有匿名性”。现在,情况发生了新变化,youTube、niconico等视频网站部分取代了录像带,某时某地观影的记忆和体验变得愈来愈淡薄。这种变化对电影和电影观众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四方田犬彦: 如今,电影已经走出了电影院,随时可以获取。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可以同时观看卓别林和陈凯歌的作品,这是一件好事情,它改变了我们的观影体验。
小时候我经常有这种想法:这部电影如果现在不看,就一辈子也看不到了。现在想看多少次都可以。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丢失了一些东西。那就是与几百个不认识的观众一同坐在黑暗的电影院里聚精会神一同观影的体验,走出电影院之后,在大街上观览展示橱窗里的服饰,到餐厅享用一餐牛排,这些活动也包含在看电影这件事的愉悦之中。今天这种体验越来越难得了。
电影在历史上有过几次大的转变,首先,静止的画像动了起来,然后有了声音,再来有了颜色,再然后变得可以携带,直至现在有了随时可以连接的视频网站。接下来的一个世纪应该还会有一两次大的变化。这并不是说电影崩坏了,而是电影的形式改变了,我觉得这没有问题。人类这种视觉动物想要观看的欲望从来没有变过,以后也还会是这样。
您在《日本电影110年》里指出,随着社交网络的发展,似乎人人都可以通过网络发表自己对电影的评价。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对这个时代电影观众和评论者又有那些期待?
四方田犬彦: 首先,我认为能自由地发表评论是一件好事情。发表评论已不再是某些人的特权了。但与此同时,这些评论具有匿名性,说起来,某些言辞恶毒,充满偏见的评论在我看来就像是公共厕所门板上的涂鸦一样,既毫无价值,又违背人性。
如果一个人想要对他人发表的作品发表评论,那他也应该清楚地表明自己的身份。这是一个道德问题。举个例子:张艺谋在自己的作品中留下名字,表明对这些作品负有责任。随意对这些经年累月制作出来的作品投去“无聊”“愚蠢”一类的指责,是很卑劣的事情,因为这些人处在匿名的状态。如果是我,就会在杂志上用“四方田犬彦”的名字写下看法,这些看法就算是在张艺谋本人面前我也能说出来,这样才算对自己发出的评论负起责任。
匿名的只言片语里既没有交流,也算不上评论。这些话可能对别人造成巨大伤害,然而写下这些话的人却始终处于安全地带。这样的事就发生在近十年间,这不只是电影评论的问题,更关乎人的道德。
 打印本文
打印本文  关闭窗口
关闭窗口